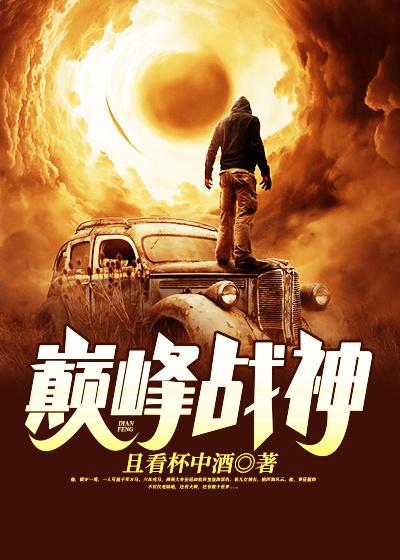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他人真好 > 第26章 不同(第3页)
第26章 不同(第3页)
绣球花已经浇完了水,路屿舟蹲在花盆前观察枝叶,拱起的背骨像一座小山丘,尚有青涩和单薄。
他听到身后人走动的声音,没回头,指着绣球花,耐心地讲了几点注意事项。
盛遇拿了根冰棍,刚拆开,只捕捉到一句话——
“你要亲自过来捯饬这些花?”
路屿舟站起身。
这种天气,稍一活动就起一层薄汗,他走到水槽边洗脸,说:“不然呢?这一排绣球花、二楼的向日葵、后院的小葡萄藤……什么时候施肥,怎么打理,你记得住吗?”
记倒是记得住,但盛遇是个生手,还是个仙人掌都能养死的生手。
这些花花草草至今没蔫,一靠上一任主人路屿舟打理得好,二靠这些植物生命力顽强。
“靠我肯定不行,但你来来回回,这也太……”
盛遇靠在门口啃冰棍,边啃边纠结。
他想说,这也太麻烦你了。
喜鹊巷和风铃北路虽间隔不远,可来来回回,又要兼顾学业,怎么看都浪费时间。
路屿舟洗完脸,把头发往后抓,睫毛垂了下来,似在思索。
片刻的沉默过后——
盛遇:“要不你搬回来住吧——”
路屿舟:“确实挺打扰的……啊?”
盛遇又啃了一口冰棍,大概听清了路屿舟未竟的那句话,皱了皱眉,“我没觉得打扰,就是怕浪费你时间,这里原先就是你家,你要是不嫌我烦,搬回来呗。”
“……”
路屿舟站在水池边,好半晌无语地笑了一声,微微挑起眉,潮湿的眉眼有点似笑非笑的意味,“我还以为你要把这些东西拆掉……搬回来就算了,这套房子就这么大,挤两个人不方便,你住吧,棋牌馆挺好的。”
盛遇觉得他逻辑有问题,“房子不小啊,你跟夏扬还挤一间房呢,没见你嫌弃过。”
“那不一样。”路屿舟懒散地应了一句,重新蹲下身,拿起剪子,修剪绣球花的枝叶。
盛遇追问:“哪儿不一样。”
剪子咔嚓一声,路屿舟下意识答:“你跟夏扬不一样。”
“……”
盛遇天塌了。
路屿舟要是故意讽刺,他还能当没听见,毕竟这人无差别攻击,那嘴属鹤顶红的,不刺挠一句不痛快。
偏偏路屿舟是无心说的。
庭院安静了好一会儿,盛遇舔着化成糖水的冰棍,莫名有点尝不出滋味。
冰棍有点怪味,涩涩的。
“……也是。”静默了几秒,他把剩余的冰棍咬碎了咽下去,泰然自若地找补:“你跟夏扬认识多久了,咱俩才认识多久,不能相提并论。”
话是这么说,可盛遇心里已经有一把巴雷特,瞄准点就在路屿舟额头,要是这人敢说一声“是”,下一秒就把这王八蛋突突掉。
友情是不讲先来后到的。
盛遇有很多朋友,不乏幼时相识,十多年的交情,但那些朋友跟路屿舟都不一样。
路屿舟在他这里,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。盛遇以为这种特殊是相互的,就像他们心照不宣地在夏扬面前装刚认识,其实私底下约着一起刷题吃饭甚至数星星。
但路屿舟现在把他排出了亲密朋友的范围。
这让盛遇觉得自己是个蠢蛋。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路屿舟总算反应过来话中的歧义,站起了身,拎着剪子回头看他,“重点不是我嫌不嫌弃,你住惯了套间,家里再塞一个人会不自在,会打扰你,夏扬不会,我跟他小时候就这么应付着过来的。”
盛遇哦了一声。
他很想说,怕打扰别人,也是一种隐形的排斥,人只会打扰自己潜意识里更信任的人。
但转念一想,这话未免有点钻牛角尖,不像他的作风。
“逗你玩的。”盛遇弯起眼睛一笑,口吻轻松愉悦,像是压根没放在心上,“能逼我们惜字如金的路大帅哥说出这么一大段话,我可真牛逼,没事,我就提一嘴,反正钥匙在你手里,你啥时候要打理这些花,自己进来就行,不用提前跟我打招呼。”
路屿舟紧盯他片刻,敏觉地捕捉到笑容背后的低气压。
“不是——”路屿舟欲言又止地逼出两个字,又顿住。
他想反驳,但具体是哪儿不一样,一时之间还真说不上来。
是啊……两人有什么不同?
他有刹那的茫然。
坚固的自我认知似乎被盛遇的追根究底敲开了一个小豁口,一点点细微的思绪在豁口一闪而过,但太快了,他没捕捉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