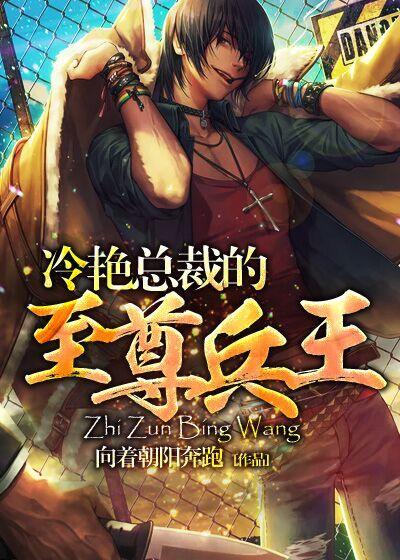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被我坑过的男主都重生了(快穿) > 第073章 被吊成翘嘴了(第1页)
第073章 被吊成翘嘴了(第1页)
不然他何以如此心魔横生,何以就这样渡劫失败?
在昏暗的室内,纪云成只将似华紧紧握住,他的眼中飘飘荡荡的,最终唤出了一直埋在他神识深处滋养的本命灵器。
纪云成作为纵横天下的大乘魔修并不用剑,但此刻浮现在空中的,却赫然是把通体素白的长剑。
与他自己、与整个室内满溢的魔气截然不同,它身上的灵气甚至比似华还要更纯净几分,其上镌刻着二字却霜。
他前世在华清宗,真霄选了他,又觉得他没用,大失所望,可是他又做错了什么,不过是天资如此,被架在火上烤,就算他在后山上练上几万次剑,拼尽全力也根本无济于事。
周围人也戏弄他纪云成,所以遇见唯一正眼看他的那剑修的时候,当对方愿意听他讲话,愿意陪着他回故居走一遭,甚至在他生辰赠了把这剑,不说来由,不说价值,只说唤作却霜。
纪云成就算是现在依然能够清晰的记得那年的所有事情,少年看着他,只看着他,就连眼底甚至有了些像是因为他而出现的温度。
他记得他那时候的嗓音,记得每一句话,记得每一个字。
陆承嗣说,“愿祝我友云成。”
我友云成、我友云成。
他反复念叨着这四个字,只觉得对方那样好,活像是画里的人出来可怜他了,是纪云成整个晦暗无光的前半生唯一可以称得上快活的事情。
雨吹芭蕉,雪落长峰,这段年岁里只要想到或许他来华清宗,或许被选上,或许被欺负,都是为着遇见陆承嗣,纪云成也实实在在是心甘情愿的。
在他小心翼翼的查了东扬陆家是什么样的存在之后,升起的不安与自卑让原本就勤勉的纪云成更加不要命的般练剑,同时又不由得希冀他们能够有并立的一天。
如若陆承嗣是回陆家,他就去给陆家做牛做马。
如若陆承嗣留在华清宗,他就做他的峰下看门打扫的随从。
就算一切都不成,他就是再托生成那少主的一条看家护院的狗也情愿。
甚至有人故意告诉他那些旧事的时候,纪云成也完全不会相信,在他眼里陆承嗣简直是天地间最好的人。
对方怎么可能会妒恨他。
再后面的事情纪云成也说不清,也记不太清楚,但既然已经讲不清爱恨哪个更多,那他们就分明该一直纠缠下去。
万籁俱寂中,自他影子伸出的心魔愈发可怖,至于纪云成那点扭曲的恨意,在万般苦痛与那点被纪云成反复不住回想着的短暂年少时光之间,最终真真正正的变了味道。
他坐在黑暗中,长长久久的出神看着并立的两把长剑,分明未做任何表情,但却无端的让人觉得这青年周身寂寥。
现如今又该说什么。
他就是犯贱,就是对陆承嗣起了不该有的心思,超出友人,他就是见不得别人去接近对方,他就是因为那剑修才变成如今这样。
论情谊,他纪云成早年与陆承嗣在后山习剑,又同伴相游,得之相赠却霜;论旧怨,他在深渊足足待的一百三十二年,最后心魔如此至重,乃至死于雷劫,天下从未有过。
无论爱恨,谁都比不过他和陆承嗣的纠葛,对方不该负责吗?都分明是他欠着他的。
对,是了,就算再活一次,他不管做什么,都是陆承嗣欠的他。
纪云成缓缓的将手放在双剑之上,周围愈发癫狂四溢的魔气,最终随着却霜重新没入他的识海中一同被压制下去,四周无波,唯独只剩下青年独自坐在床沿,望着似华时眼底悄然簇生而出的幽幽暗火。
既然毁了他的大道,就合该再赔一个人给他——
此前纪云成对陆承嗣无论是什么感情,但全无越轨举动,也自然丝毫生不出这种额外心思。
自从想清楚了之后,豪言壮语也放了出去,纪云成却在第一步真正的犯了难。
他记忆里除了打打杀杀的之外,与情爱相关的人事物,唯一可以称得上参照的就是那些女魔修,但真的叫他学着那些痴缠浪荡的模样,拉下脸去勾陆承嗣,却又是万分不能的。
可若是走强迫的路线,反倒是纪云成不大情愿。
因而直到一行人都快要回华清宗的时候,纪云成终于给自己想出来个解决办法。
他先隐姓埋名的试探一二,看陆承嗣的反应,再做其他打算。
而陆承嗣再见到纪云成的时候,叩门而入的青年已然收拾规整,就连一贯散漫荡浪的神情都沉静了下去,躬身行礼道:“全托小师叔不计前嫌搭救,那妖魔残留下来的魔气已经消失。”
对方话毕,只恭恭敬敬的将似华递了上来,倒真的像是浪子回头,诚心悔过。
“告知所有人,明日动身回宗门。”
不过事出反常必有妖,他倒是期待纪云成能做些什么。
低着脑袋的纪云成也尚未发觉,他听着对方的声音,满心满眼想的却全是该如何下手。他将似华送回,好让陆承嗣明明白白的知道,就算只是试探,也是反抗不得的。
只在当晚,剑修原闭目静思,却忽地有一阵怪风桌上烛台忽地打灭,整个厢房内只落在了彻底的黑暗之中,甚至连外头的月光都无法进入半分。
尽管椅子上剑修的坐姿依旧规整,但实际上他的身体早已经因着这等威压而丝毫动弹不得。
而陆承嗣轻轻睁开眼睛,只平静的看着四周满溢的魔气,好似尚未觉察出自己已然身陷囹圄。
总算有点动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