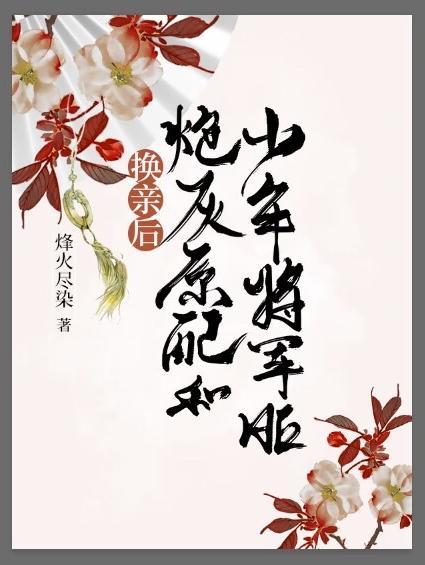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冰花 > 重归于好(第2页)
重归于好(第2页)
随权被她甩开,又好气又好笑,耐着性子哄:“看什麽帅哥?我不就是?看我行不行?”他凑近了些,试图用自己挡住她的去路。
塞梨停下摇晃的脚步,眯起醉眼,认认真真丶上上下下打量了随权几秒钟,然後非常果断地丶嫌弃地一挥手,把他推开:“你……还是算了吧!”说完,更加用力地拽着簪冰春就要继续她的“寻男大业”,结果自己脚下一个趔趄,差点带着簪冰春一起摔个结实。
法斯文一直冷眼旁观,此刻动作极快,长臂一伸,稳稳地抓住了簪冰春的另一只胳膊,将她从塞梨的“魔爪”和倾倒的边缘拉了回来。
随权和孙偏隐也赶紧上前,一左一右架住了摇摇晃晃丶还在嚷嚷着“看男人”的塞梨。
簪冰春被法斯文拉着,站稳了身体,擡头看向他。
法斯文的目光锁在她脸上,深邃的眼底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和灼热,声音低沉,清晰地穿透了塞梨的嚷嚷:
“今晚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像是在确认她的注意力。
“哄我。”
他清晰地吐出条件。
“我就原谅你。”
他话音刚落,被随权架着的塞梨像是捕捉到了关键词,猛地扭过头,冲着法斯文的方向,响亮地丶带着醉意的鄙夷“哼”了一声,声音拔高,充满了挑衅:
“哄你?!”
她舌头打结,但气势不减。
“你配吗?法……法斯文?!”
簪冰春的目光从法斯文脸上移开,落回还在挣扎的塞梨身上。她看着塞梨醉醺醺却异常执着的样子,忽然,嘴角极其轻微地向上弯了一下,一个很淡丶却带着点真实兴趣的笑容。她转过头,重新看向正等着她回答的法斯文,声音平静,却带着一种出人意料的附和:
“其实……”她顿了顿,看着法斯文瞬间变得有些错愕的眼神,清晰地说,“我也想去看。”
法斯文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一瞬,随即被一种又好气又好笑丶还带着点咬牙切齿的情绪取代。他盯着簪冰春那副“认真”想去“看男人”的表情,磨了磨後槽牙,突然嗤笑一声:
“我长得……也不差吧?”他的声音带着点自嘲,又带着点不容置疑的自信,目光紧紧锁着她。
簪冰春迎着他的目光,没有任何波澜地丶极其敷衍地应了一声:“哦。”
这个“哦”字像是最後一根稻草。
法斯文不再废话,抓着簪冰春胳膊的手猛地收紧,力道不容抗拒。他二话不说,拉着她转身就走,步伐又大又快,目标明确地朝着停车的地方去,完全无视身後塞梨瞬间爆发的丶更加响亮的抗议和呼喊。
“哎?!簪冰春!回来!看……看帅哥去啊!”
“法斯文!你……你放开她!”
“随权!你……你死人啊!拦住他!”
塞梨气急败坏的声音被夜风远远抛在後面,越来越模糊。
法斯文充耳不闻,只紧紧攥着身边人的手腕,大步流星,仿佛身後追赶的不是醉鬼的叫嚷,而是他等待已久丶终于抓住的机会。
车内空间狭小安静,引擎低鸣。法斯文的手没松开,反而攥得更紧,牵引着簪冰春微凉的手,不由分说地贴上了自己的脸颊。他的皮肤温热,带着夏夜未散的燥气,还有一点刚硬的胡茬触感。
“簪冰春,”他侧过脸,迫使她的掌心完全贴合他的颧骨,目光灼灼地锁住她有些躲闪的眼睛,声音低沉执拗,“看我。我……不差。”像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孩子。
簪冰春被迫迎上他的视线。灯光滑过他深邃的眉眼,挺直的鼻梁,紧抿的唇线。那张脸,无论看多少次,依旧有瞬间夺走呼吸的力量。她的呼吸真的停滞了片刻,胸腔里的空气像是被抽空,随即才像溺水的人浮出水面般,急促地丶微微地喘息了一下。
这细微的反应被法斯文精准捕捉。他眼底的紧张褪去一丝,染上更深的探寻和某种势在必得的决心。他维持着这个近乎禁锢的姿势,声音放得更低,带着点诱哄的意味,清晰地提出交换条件:
“我哄你,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很轻,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,像羽毛拂过心尖,“哄你……你原谅我,行不行?”这是她第一次如此直白地丶放下所有防备和骄傲的求和。
法斯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,立刻点头,动作快得像怕她反悔。他的目光紧紧攫住她,每一个字都清晰沉重,带着尘埃落定的宣告:
“行。我原谅你。”他顿了顿,眼神深邃如海,翻涌着压抑了太久的情感,“我们,重归于好。”
簪冰春看着他眼底汹涌的丶不容错辨的认真和期待,那颗悬了三年的心,终于重重落回实处。她也轻轻点头,幅度很小,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决绝:“嗯。”
得到这个肯定的回应,法斯文像是被解开了最後的束缚。他身体猛地前倾,带着不容抗拒的压迫感,瞬间拉近了两人之间那点可怜的距离。簪冰春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,浓密的睫毛如同受惊的蝶翼般剧烈颤抖着,泄露了她内心的汹涌。
下一秒,温热的丶带着他独特气息的吻,精准地丶不容置疑地落在了她的唇上。不是浅尝辄止的触碰,而是带着三年思念丶委屈丶失而复得的狂喜和绝对占有的力道,深深地烙印下来。一个漫长到几乎让人窒息的吻。
唇齿稍稍分离,法斯文的额头抵着她的,呼吸灼热地喷洒在她脸上。他的声音带着吻後的沙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丶残馀的脆弱,固执地再次追问,像要一个永恒的保证:
“簪冰春,”他叫着她的名字,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执着,“我很差吗?”仿佛刚才那个强势的吻只是虚张声势,他心底深处依旧盘踞着被她推开丶被她评价“挺差劲”的阴影。
簪冰春在他怀里,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胸腔里同样剧烈的心跳。她用力摇头,发丝蹭着他的下颌,声音带着点被吻後的微喘和前所未有的肯定:“不……不差。”这一次,没有犹豫,没有敷衍。
法斯文似乎因为这个答案而深深吸了口气,抱着她的手臂收得更紧,仿佛要将她嵌进自己的骨血里。他埋首在她颈窝,声音闷闷地传出来,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丶近乎乞求的脆弱:
“那你以後……”他顿了顿,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,带着对未来的全部期冀和恐惧,“别离开我了,行吗?”
以後?
这个词像一道光,劈开了她心中最後残留的阴霾和恐惧。那些关于“配不配”丶“还不还得起”的挣扎,那些害怕被再次抛弃的梦魇,在这个温暖的丶带着颤抖的怀抱里,在他卑微又固执的乞求面前,瞬间土崩瓦解。
她不会了。
这一次,她好像……真的再也不会推开他了。
她缓缓擡起手,迟疑了一下,最终小心翼翼地丶带着点笨拙的珍重,回抱住了他紧绷的背脊。将脸更深地埋进他散发着熟悉气息的颈窝,用行动代替了回答。无声,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