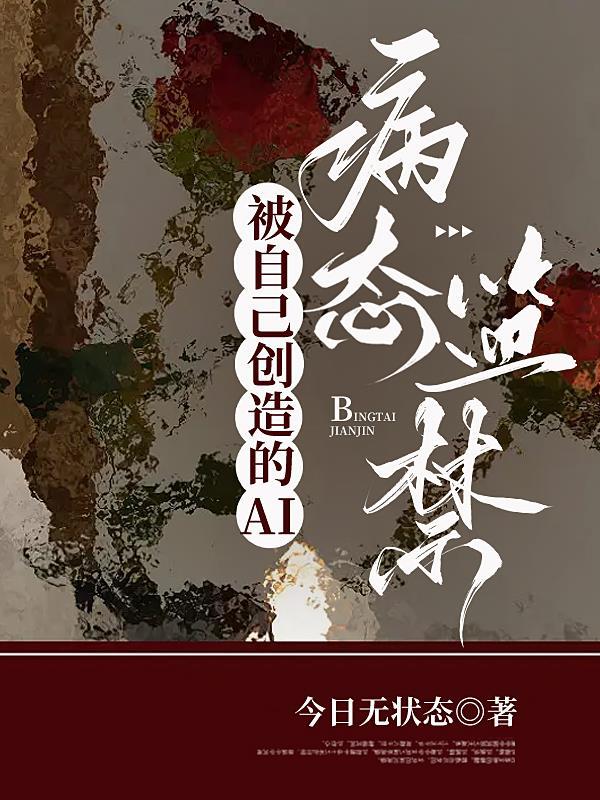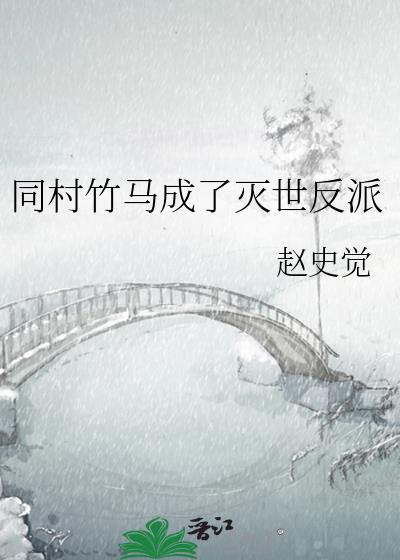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我在精神病院给人算命以待飞升 > 第119章 同袍(第2页)
第119章 同袍(第2页)
“没,没有……”
路窈伸手拿起那封奏折。
“牝鸡司晨?这话我听着耳熟。”她嗤笑一声,“我上任的时候就听厌了,怎麽一年了,御史台骂人的词儿还没翻新?”
马文博扑通跪倒,额头重重磕在青砖上:“国师大人功在社稷,岂是这等混入军营的贱婢能比!”
“说来可笑,公鸡不打鸣,母鸡打了鸣,却成了罪过?”路窈冷哼,“阎王帖发作那日,你连脉都不敢诊。你马文博不敢治丶不会治的病,她治了,反倒是她该死?”
马文博浑身一颤,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,却仍强撑着狡辩:“国师明鉴!下官丶下官当时是担心贸然接触病患,反而会加速疫病传播啊!”
他膝行两步,官袍在地上拖出凌乱的痕迹:“这丫头不过是误打误撞……”
路窈闻言轻笑:“好一个误打误撞。”
她突然推开雅间的雕花窗,朝楼下熙攘的街道一指:“正巧,那位卖炭翁咳了半月有馀。马太医既觉得季姑娘医术不精,不如当场比试?”
路窈广袖一拂,小太监将街角那个佝偻的老翁请上了雅间。
老人脸上还沾着煤灰,每咳一声都带着破风箱似的杂音。
“季太医先请。”
季念安深吸一口气,扶老翁坐下。
她指尖搭上老人树皮般粗糙的手腕,忽然眉头一皱:“可是夜卧盗汗,痰中带血丝?”
见老翁连连点头,她迅速拈起金针:“肺络受损,需先刺太渊丶列缺二xue。”
马文博插嘴:“胡闹!这分明是肺痨。”
季念安头也不擡,针尖已精准刺入xue位,“老丈指甲发紫,舌苔薄白,分明是炭尘积肺。”
她手法娴熟地运针:“若按肺痨治,怕是要出人命。”
银针离体的瞬间,老翁突然剧烈咳嗽,吐出一口浓黑的痰块。
老翁抚着胸口,浑浊的眼睛渐渐清明,“哎呦……这口气可算顺了!”
他颤巍巍站起身,朝着季念安就要下跪,“多谢这位公子救命之恩!小老儿这半个月咳得半条命快没了。”
路窈拦住他下跪的动作,眼中闪着狡黠的光,“老丈若知道,这位‘公子’其实是位小娘子呢?”
季念安一惊,没想到路窈竟然这样随口就将她女子的身份说了出来。
“怎麽?我们季太医莫非舍不得这身男装?”路窈笑笑。
“不是……”季念安愣住。
老翁瞪大眼睛,煤灰斑驳的脸上先是惊愕,继而绽开朴实的笑容:“管他是公子还是娘子,能治病的就是好郎中!老婆子常说俺眼拙……那就多谢小娘子救命之恩!”
季念安望着眼前这一幕,唇角微微扬起,眼眶却渐渐泛红。
多少年了,她第一次不必掩饰女儿身份,不必压低嗓音说话,就这样以女子之身,被人夸赞为好郎中。
“不错,季念安就是女子,无需遮掩。老丈明白人,可惜这世间多的是糊涂鬼。”
路窈抚掌而笑,“这封奏折,我明日在早朝亲自呈上。我倒要问问御史大夫,这天下病症,可会因医者是男是女而挑三拣四?”
季念安望着路窈手中的奏折,胸口突然涌上一股滚烫的热流。
她想起自己十岁那年,偷偷趴在医馆窗外偷看郎中施针,发现後被毒打了一顿。
十五岁时,她女扮男装去药铺当学徒,每晚都要用竈灰把脸抹得黝黑。
而今,这位国师竟要为她,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医女,在金銮殿上质问满朝文武。
多少年来,她一直以为只要医术够好,男装穿得够像,就能在这世道挣得一席之地。
却从未想过,有人会为她掀开这层僞装,让她堂堂正正地以女子之身站在阳光下。
季念安擡头,正对上国师含笑的眼眸。
那目光清澈如泉,映着她泛红的眼眶。
这一刻,她忽然明白了路窈那句“同袍”的真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