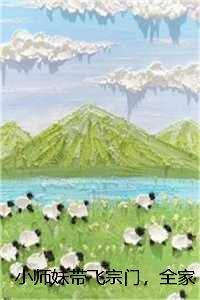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任务失败,但反派自我攻略了 > 120130(第23页)
120130(第23页)
似是讶异于这垂死反扑的力度,他身形倏然后撤半步,袖中一道清光流转的玉尺滑入掌心,抬手便挡。
“铛!!!”
金铁交击般的巨响炸开,魔焰与清光**撞,激荡的气流将周遭积雪轰然掀飞。
印飞白到底是不敌。
这一击之后,他踉跄倒退,胸前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崩裂开来,黑血汩汩涌出,气息瞬间萎靡下去。
而祁若衡仅退了半步,玉尺光华依旧,衣袂飘飘,连发丝都未乱一分。
高下立判。
印飞白单膝跪地,以手撑地,大口大口呕着黑血,抬起头死死盯着祁若衡,眼中疯狂退去,露出一片清明。
祁若衡垂眸看他,如同俯瞰一堆再无价值的垃圾。
他缓缓抬起了手中的玉尺。
尺端清光吞吐,杀意凛然。
单膝跪地的印飞白忽然抬起头,朝着那口敞开的黑棺,嘶声怒吼:“你他娘的——!!!”
“你还打算睡到什么时候?!”
吼完,他吐出一口黑血,怒气冲冲地站起身踢了一脚那口棺材,“非等老子被打成这副鬼样子,你才肯出手是不是?!宋、默!!”
最后两个字,他是用尽所有力气喊出来的。吼声在凌剑台上空隆隆回荡,震得无数人耳膜发麻。
而下一秒,祁若衡斩落的玉尺,骤然僵在半空。
他的杀机,被生生打断了。这世上还有谁,能够硬生生截断他的杀机?
他猛地扭头,盯向那口漆黑棺椁。
凌剑台一片死寂,风雪也停住了。
然后。
“咔”的一声。
一声极轻、极脆的响声,像是有人在舒展筋骨,从棺中传来。
紧接着,在无数道惊骇欲绝的目光中,棺内那只苍白修长、本该毫无生气的手,扶上了棺沿。
紧接着,那双紧闭的眼睫,轻轻颤了颤。
在全场死一般的凝固中,在祁若衡骤然收缩的瞳孔注视下,在印飞白嘶哑癫狂却又隐隐透出快意的喘息里。
棺中人,缓缓睁开了眼睛。
那是一双极黑、极深的眼睛。初睁时,眼底空茫如永夜,没有焦距,没有情绪,仿佛连魂魄都未曾归位。可仅仅一瞬,那空茫便如潮水般褪去,某种冰冷、沉郁、令人心悸的东西,一点点从深处浮起。
他转动眼珠,视线极其缓慢地扫过周遭,掠过皑皑积雪,掠过如林巨剑,掠过一张张写满骇然与难以置信的脸,最终,落在了高台之上、手持玉尺的祁若衡身上。
然后,他微微偏了偏头。
一个极其细微的动作,却让祁若衡握着玉尺的手指,猛然攥紧,骨节发出“咯咯”轻响。
棺中人喉咙里溢出一声模糊的低吟,像是许久未曾使用的器具,艰涩地磨合。他撑着棺壁,慢慢坐起身。
他就那样坐在棺中,在众目睽睽之下,拔出了插在胸口的匕刃。
所有人都僵住了。大脑一片空白,连呼吸都忘了。魔尊温如晦……不是死了吗?不是被温禾亲手诛杀、尸身都被祁若衡暗中藏匿炼制吗?怎么会……怎么会坐起来?!
这超出了所有常理,颠覆了所有认知。
叶不归微微侧眸,看向身侧的小徒弟。
温禾依旧端坐着,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,背脊挺直,目光平静地望着台上那惊悚的一幕。
可叶不归看见,她紧绷的肩线,终于放松了下来。然后,在那无人注意的、被广袖遮掩的唇角边,极轻极快地勾起了一抹转瞬即逝的如释重负的笑容。
叶不归眸光微动,什么也没说,只将视线重新投向台上,思索着该挑个什么时机带着她的小徒弟逃跑。
而台上,温如晦终于完全睁开了眼睛。
他抬起手,看了看自己苍白的手指,又缓缓抚过胸前那道伤口。指尖触碰到皮肉翻卷的边缘时,他“啧”了一声。
然后,他抬起眼,再次看向祁若衡。
这一次,他开口了,声音低哑,缓慢,听着却令人脊骨都发寒:“祁宗主。”
他轻轻歪了歪头,像在打量一件有趣的物事。
“好久不见。听说你想把我练成傀儡?我还以为你们正道人士应该会嫌我们魔族肮脏得不得了,真是难为你了。”
祁若衡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。他死死盯着棺中坐起的那人,握着玉尺的指节因过度用力而青白狰狞,手背上甚至浮起根根血管。
“不可能……”他声音嘶哑,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,“你不可能还活着!”
温如晦闻言,低低笑了一声。他慢条斯理地撑着棺沿,从棺中跨了出来。这具身体确实沉睡了太久,导致他动作都有些滞涩,但他站得很稳,玄黑袍摆在风雪中微微拂动。
他低头,再次看了看自己胸口的伤,指尖轻轻按在那狰狞的边缘。
“是啊,”他自言自语般轻声道,“照理说,是该死了。”
随后又看着祁若衡笑道:“但有个人不想让我死,那我只好先活着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