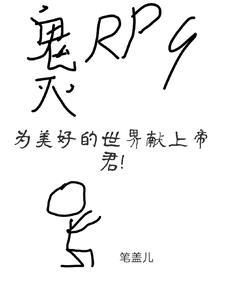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本官死后 > 第123节(第2页)
第123节(第2页)
但对于宗遥来说,这样的沉默,其实就已经是答案了。
于是她自嘲地笑了笑,深吸一口气,又问道:“那么,我换个问题,阁老曾是杨家门生,又与杨升庵互为知己,那您可知道,宗、杨两家,究竟是什么关系?”
颜惟中忽然道:“你做大理寺少卿时,老夫曾见过你。当日只觉得似曾相识,甚是面善,却并未多想。”
“……”
“直到你女身之事东窗事,麦大监着锦衣卫查得你来自宣城,老夫才恍然惊觉你的身份。”
“……”
“昔日老夫做客杨府,升庵曾指家中一少年示我,说,此乃家中幼弟,虽是外室所生,从了母姓,却得杨家接纳,被抱回府中抚养。这名外室所生之子,还未及成年改姓,便私自与一民女私奔离府,惹得杨辅震怒,却反而幸运地逃过了杨氏一族的灭顶之灾。”
说着,颜惟中缓缓抬眸,看向那毛笔悬停之处。
“你的眉宇之间,有几分像你生父少年之时。”
第146章勿相负(十)
周隐愣住了,望着身侧的宗遥:“那你也是杨……杨……”
宗遥深吸了一口气,像是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悲愤一般,提笔蘸墨,所书字迹凌冽如刀锋。
“到底是有多深的怨恨,贬官不够,流放不够,只是回来替生父守孝收敛尸骨,就要疑心大起,屠灭全村?!他不是早就大获全胜了吗?杨家一没叛国,二没谋反,杨家也早在大礼议失败之后就被全部逐出朝堂,再不可能对他有任何影响……难道,这还不够吗?”
“一介臣子,妄想自己能够左右天家,本身就是谋逆。”颜惟中淡淡道,“杨廷和如是,颜庆如是……林言,亦如是。”
那支悬停在半空的笔砸落下来,喷溅的墨点污在纸上,有如绽开的黑色血花。
“论治国辅政,我不如杨廷和。论揣测帝王心意,我不如庆儿。若才学政绩,我不如林言。”颜惟中慢吞吞地捋着花白的胡子,“但最终,是老夫留到了最后。老夫比他们都强的,就是老夫时刻都恪守臣子的本分,从不逾距。天家需要能臣,但能臣总是一时的,若是骄纵成狂,那这朝堂之上,又该成谁家天下?”
*
林言今天白日里又在狱中给陛下上书。
即便他此前托锦衣卫转交出去的手书都如石沉大海,但却仍旧没有丝毫的放弃。
就连对面牢内的曾铣都在劝他:“大不了就是一死!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没有做过!即便今日亲赴黄泉,他日,后世自会为我们沉冤昭雪!”
可林言还是在不知疲倦地写,直到锦衣卫那些人倦了,烦了,明确告知不会再向他提供任何笔墨,他便撕下囚衣上的布条,咬破自己的手指,蘸着血接着写。
这些日子一直缩在角落里啜泣的林鸿,看着自己记忆中睿智威严的父亲,如今竟蓬头垢面,衣衫褴褛,像个老疯子一般满手满身都是血,终于绝望地意识到自己或许再也没有逃出生天的一日,崩溃地大叫了一声,猛地撞向牢内坚硬的石墙:“呀——!!!”
一身吃痛的闷响,他拼了一身狠力,最终却没能感受到多少头破血流的钝痛,张惶地抬起头来,却见往日厌恶的兄长,正拦在自己身前,面色苍白地低头看着自己。
他吓得惊叫了一声,跌坐在地上。
林照捂着被他重创的腹部,满头大汗地深吸了几口气,才开口道:“你母亲还在外面等着你……别让她失望。”
林鸿呆呆地看着他。
林照没再言语,他似乎是被那一下给撞狠了,捂着腹部缓缓地重新靠坐回草蒲上,闭上眼,将身子慢慢贴上了冰冷的牢壁。
许久,耳畔传来林鸿讷讷的问话声:“我……我们会死吗?”
林照似乎很不想答话,但还是应了句:“不会。”
“为……为什么?”
“因为按照大明律,没到判死的地步。”
“那……那流放呢?”
林照“嗯”了一句。
林鸿大张着嘴许久,突然抽噎着冒出一句:“可……可是,我听说流放之地不是苦寒之处,就是湿热瘴气之所,我这辈子,还……还能见到我娘吗?”
“我连我娘的坟茔都或许再见不到了。”
林鸿瞬间被堵得哑口无言,停在那里好半晌,才不服气地哼了一句:“那你让我撞死在这里就能报复我娘了,反正你也一直不喜欢她。”
“你撞头会溅血,这牢中已经很脏了。”
“你……!”
林鸿一副被他气得要杀人的模样,要不是在牢里,多半就要扑上去掐死他了。
他就知道,林衍光就是个王八蛋!什么狗屁兄长!亏他刚才还觉得他有几分像人!
说着,他用力地哼了一声,抱着手,又重新靠回墙角,脑海中不断编纂着如何将林照下油锅,扒皮抽筋的画面,一时间,连死都不想寻了。
而另一头的林照极轻地咳嗽了一声,口中腥甜被强行尽数咽下。
林鸿那小子这些年被养得壮如牛犊,遭那一撞,险些将他半条命都给去了。
锦衣卫昭狱之中除非将死不得用药,他伸手搭在脉上给自己诊了一脉,心肺尚可,只得默默忍下,任凭腹内翻江倒海般的痛楚将他逐渐淹没……
不知过去了多久,他察觉到面颊上似乎有扑簌滚烫的水珠溅上,周身柔软舒适有如漂浮在紫藤香沁满的云端之中。他费力地睁开眼,缓缓抬手,想要去拭眼前之人的泪珠。
她俯下身来,将脸凑到了他手指边,红着眼睛道:“那些锦衣卫是不是对你用刑了?我才走了几日,你怎么伤成这样了?”
他摇了摇头,轻笑:“一时不查,被一条疯狗咬了一口,只是看着严重,没什么大事。你从宣城回来了?那,你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吗?”
“……”宗遥顿了顿,强笑着点了下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