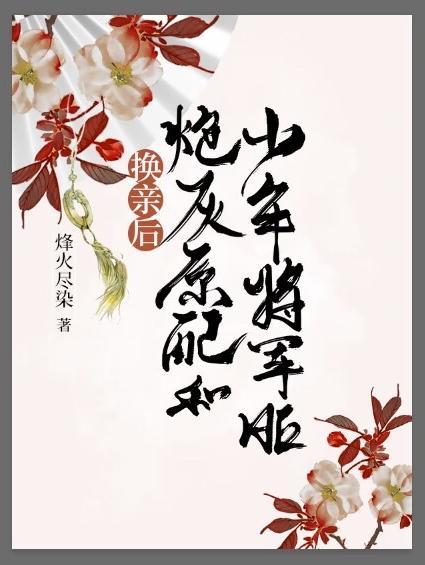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墟萸 > 第139章 双面女(第1页)
第139章 双面女(第1页)
三天的婚宴终在喧嚣中画上句点,特克斯洛城外的春风裹挟着旷野的馥郁,漫过初绽新绿的柳枝,拂得人眉宇间都染上几分舒朗。城外的送客仪式虽简朴,却依旧聚拢了人山人海——各地贵客怀揣着查理尼二世回赠的锦盒,整齐列队于茵茵草地,聆听虔世会主教老冯格的宣讲祝福。他金色三重法冠系带在风里轻颤,声如洪钟穿透人群的嘈杂,祷词的尾音缠绕着飘落的桃花瓣,落在众人肩头,仿佛神明撒下的祝福。
警戒圈外的民众踮脚张望,目光在贵客们脸上流连:这些人经三夜狂欢,个个眼眶挂着乌青,华贵衣袍皱得像揉过的纸,连帽檐的孔雀羽毛都蔫头耷脑地垂着。有人低声嘀咕:“那些海盗团的浪荡子怎么没来?”也有人现,撒不莱梅使团里那个冰雕似的美人竟也没了踪影,仿佛被晨雾卷走了一般,只留下空气中孤寂愣的撒不莱梅特使冉·杜兰特。
仪式一毕,贵客们便在骑兵护卫下缓缓离去,马蹄踏过带露的草地,留下串串浅痕,沾湿的草叶在蹄印边缘微微颤抖。围观者潮水般涌入城墙下的集市,最惹眼的莫过于那些异域客人们用过的餐具:银质汤匙映着天光,描金瓷碗泛着莹润光泽,拍卖师的嗓音扯得老高,像被捏住脖子的公鸭;即便是寻常客人用过的铜杯、锡壶、木碗,也被商贩们论斤收来,用细布擦得锃亮,摆在铺着靛蓝麻布的摊子上。铜器在阳光下淌着暖黄,木碗的纹路里还浸着果酒的甜香,引得各城镇的乡绅们围着摊子打转,指尖在器物上留恋不去。
一阵风卷着桃花瓣掠过,列拉?瓦莱在艾蒙派提王室卫队护送下骑马出城。她向迎送仪式木板台上微笑的冯格主教颔致意,目光扫过这喧闹的城外市场,嘴角浮起一丝浅淡的失落,随即催马前行道:“人总贪恋俗世的繁花,却不知每朵绽放都藏着代价。”说罢,她不经意瞥向自己缠着绷带的手臂,亚麻绷带下隐约透出暗红,此刻还在隐隐作痛,像有无数细针在刺。
身侧,查理尼二世身披金袍昂远眺,阳光在他袍角的飞狮纹刺绣上跳跃,溅起细碎的金光。他转头时语气轻松,仿佛未闻弦外之音:“还是春天最慷慨,你瞧这新抽的柳丝、初开的野菊,连风里都裹着希望的香甜。”他抬手接住一片飘落的柳叶,指尖划过那嫩绿的叶尖。
列拉?瓦莱猛扯缰绳,马蹄踏碎几片飘落的花瓣,粉色的花泥溅在马靴上。她罕见地掀起面纱,露出清丽却苍白凝重的面容,望着查理尼二世道:“我向来敬仰您的父亲,如今又见了您的为人处世之道,才知那份豪迈纯粹原是一脉相承。这真是帝国之幸。”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,目光紧紧锁住对方的眼睛。
查理尼二世依旧满面春风,俏皮地挑了挑眉,眼角的笑纹里盛着少年气讨好道:“您是说我偶尔像孩童般顽劣?”他故意放慢语,语气里带着几分戏谑。
列拉?瓦莱沉默片刻,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马鞍上的蔷薇雕花,雕花的尖刺硌得指腹微痛,留下浅浅的红痕。最终她默不作声扯马向前,面纱在风里轻扬,遮住了眼底复杂的光——有敬佩,有忧虑,还有丝难以言说的警惕,如同平静湖面下涌动的暗流。
看着列拉?瓦莱那依旧不动声色的脸,查理尼二世脸上的笑意悄然淡去,目光冷冷扫向远处的老冯格。而这位主教正与几名亲信修士低语,墨色袍角在风里翻卷如帆,不知在密谋些什么,神情诡秘。这位君王暗自错错牙,陡然扬声向卫队喊道:“都打起精神!务必安全护送列拉女士返程!”
上千巨石城精锐骑兵齐声应和,声浪震得大地微微颤。甲胄在阳光下迸射冷冽的光,马的薄铁面帘映出锐利的芒,马身红黄相间的绣花布甲随风起伏,宛如流动的火焰。系上了红缨的长矛齐刷刷举向苍穹,“呼哈”的吼声震得柳枝簌簌落芽,惊起枝头啄食的麻雀,扑棱棱掠过湛蓝的天空,翅尖划碎了几片流云,留下转瞬即逝的痕迹。
漫漫归途,众人心头似压着块湿冷的石头。野外的初春如此清新美好:新绿的草甸缀满蒲公英的金盏,溪水潺潺淌过卵石滩,冰层消融的脆响如碎玉坠地,可这一切都因那份压抑蒙上了灰白,仿佛天地间的色彩都被抽去了几分。
见列拉?瓦莱一路郁郁寡欢,鸿敦?瓦莱忙催马靠近,马蹄溅起的泥点落在草叶上,洇出小小的深色印记。他声音轻快地打破沉寂:“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奥妮成了王妃,查理尼二世总得兑现承诺,你也该松口气了。”他试图让气氛轻松些,可语气里的刻意却难以掩饰。
列拉?瓦莱身子一颤,嘴唇霎时褪尽血色,像被抽走了所有生气。她猛勒马缰,马儿不安地刨着蹄子,踢飞了几颗小石子,石子滚落在草丛里,出轻微的声响:“你那边……一切都还好?”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,带着丝紧张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鸿敦?瓦莱微微一笑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,藏着得意洋洋的果决:“那个歌手确实是他雇来的。我已给马努斯去指令,让他彻底绝了后患。”说罢松了口气,好似多日的忧虑已然烟消云散。
列拉?瓦莱猛地收住缰绳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,几乎要嵌进掌心,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:“何时的事?当真……了结了?”她屏住呼吸,等待着那个或许会改变一切的答案。
鸿敦?瓦莱扬起嘴角,风掀起他的披风,露出腰间佩剑,剑鞘的云纹在阳光下流转着暗芒,透着几分肃杀。“飞鸽昨夜已传书,一切妥当。人已抓获,他的十几名党羽当场正法,主犯正在押来的路上,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送到您面前。”他说话时,目光扫过远处起伏的丘陵,那里的阴影里,仿佛藏着无数双窥视的眼睛,让人不寒而栗。
“他还活着?”列拉?瓦莱面纱下的脸色铁青如淬冰玄铁,指尖死死绞着缰绳上的银铃,那“叮铃”脆响在寂静的旷野中透着刺骨的寒意。远处的杜鹃花海在风中翻涌,如同一大片流动的猩红血浪,映得她眼睫上未干的泪珠都泛着诡异的红光。一只乌鸦突然从花海中惊起,翅膀扫过花瓣的声音惊得她坐骑打了个响鼻。
鸿敦?瓦莱抚着花白的胡茬,指腹摩挲着胡须间凝结的晨露,嘴角勾起抹自鸣得意的笑,腰间的和田玉佩随着马匹的颠簸轻轻撞击铠甲,出“咚咚”的闷响:“像他这样的小崽子,掀不起什么风浪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列拉绷带下微微颤抖的手臂——那亚麻绷带下结痂处的血渍已渗透成暗褐色,“或许您可以亲自审问他,我让人准备好了铁钳,万一可以获得什么重要的信息。”
“住口!”列拉?瓦莱猛地扯住缰绳,黑马人立而起,前蹄踏碎了路边一朵初绽的矢车菊,紫色花瓣混着泥土飞溅。她暴怒地死死盯着鸿敦?瓦莱,面纱下的眼神仿佛要化作利刃将他碾碎:“永远不要自以为是!”狂风掀起她的轻纱,露出下颌紧绷如弓弦的线条,“我只想看到他的人头!”话音未落,她斗篷下的手已按上腰间的短剑,剑柄上的宝石在阳光下闪着狠厉的光。
望着列拉那罕见的愤恨之色,鸿敦?瓦莱慌忙向身后侍从勾手,无名指上的金戒指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:“快马去给马努斯传话,把桑格的人头送来!”说着摘下指头上的印鉴戒指扔过去,戒指在空中划出一道金黄弧线,“去归,耽误了时辰提头来见!”
亲信慌忙将这枚戒指塞进怀中的鹿皮袋,向身后打了个呼哨,那哨声尖锐如鹰啼。十几名瓦莱家骑兵立刻拨转马头,马蹄扬起的尘土混着野蔷薇的甜香,在晨雾中拖出一道黄龙,很快消失在通往坎帕尼的驿道尽头,只有渐行渐远的马蹄声还在旷野中回荡。
看着这些干练的骑兵离去,列拉?瓦莱扯马驻足良久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马鞍上的夜枭雕刻,眉头紧皱陷入沉思。鸿敦?瓦莱回头瞟了眼她稍缓的神色,忙讨好道:“咱们是回天鹅堡,还是去坎帕尼?”远处的一座磨坊风扇正迎风迟缓的转动,咯吱作响让人愈心烦意燥。
列拉?瓦莱沉默片刻,轻纱下的面容染上几分惆怅,她垂脸望着马鬃间缠绕的野蔷薇,粉色花瓣上的露珠顺着鬃毛滚落,出不知是啜泣还是哀叹的声响:“鸿敦,我信任你,甚至过你对自己的信任!”话音未落,她猛地抬头,目光如鹰隼般死死盯着这位两鬓斑白的家族元老,面纱下的嘴唇因用力而抿成一条直线,仿佛要咬碎口中的话语。
鸿敦?瓦莱忙用力弯腰行礼,隆起的大肚子将衣服下的软锁甲顶得“咯吱”作响,他急促喘息着,既有身体的挤压,也有内心的敬畏:“我知道属下愿为您赴汤蹈火!”他的声音因激动而颤,膝盖处的铠甲摩擦着马腹,留下深色的汗渍痕迹。
“但是”列拉?瓦莱面露哀伤地望向阳光下开满春花的田野,蒲公英的绒毛在眼前飞舞恍动着人的心境,她声如呢喃般道:“人总是会因面对诱惑而迷失自己。”她伸手接住一朵飘落的花絮,在指尖轻轻搓揉,“那些诱惑如同魔鬼,虚幻而又如此魅惑,让人飞蛾扑火,即使明知那是个迷梦!”
鸿敦?瓦莱忙扯马凑近,再次将手臂按在胸前,弯腰时银质腰带扣撞在剑鞘上出“当啷”脆响:“我明白,就如您曾经说过的,人往往抓不住最美好真实的东西,”他望着列拉?瓦莱面纱上隐约可见的玫瑰暗纹,那些淡银色的花瓣已被泪水浸得暗,“却被虚妄的诱惑拖入绝境,就像飞蛾扑向燃烧的蜡烛,最后只剩随风而去的尘埃。”
列拉?瓦莱松了口气,回头望了眼身后护送的上千名巨石城精锐铁甲骑兵——他们的铠甲在阳光下连成一片银色的海洋,破例缠在长矛上的红缨如同一簇簇燃烧的火焰,甲叶碰撞声在旷野中汇成沉闷的雷鸣。她犹如陷入迷梦般迟钝地转过头,声音带着丝颤抖:“希望你能感受到这样的信任”她紧紧盯着眼眶红润的鸿敦?瓦莱,深深吸了口气,眼泪不受控制地从眼角滑落,打湿了面前的轻纱,透出底下苍白如纸的肌肤,“就如同西阿翁”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看着已然泣不成声的列拉?瓦莱,鸿敦?瓦莱被这个表面强硬内心敏感的女人深深触动。他用力扯马凑近,想要伸手拥抱宽慰,却被两匹马之间的距离阻隔,只能无奈地垂下肩膀,关节出“咔嗒”的叹息:“您给了他那么多,也宽容他那么多次背叛”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,像被砂纸磨过的橡木,“他却偏要飞蛾扑火,这不是您的错,您已经尽力”
“这就是命运!”列拉?瓦莱缓缓抬起头,微微掀起面纱,用绣着鸢尾花的丝帕擦着脸颊的泪珠,嘴角勾起抹似笑非笑的神色。风吹散了她的面纱一角,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,他是铁格安排到我身边的人。”她的指尖抚过缠着绷带的手臂,如丝绸般的指腹微微颤抖,“但我每次都给他足够的空间,甚至在铁格死后还希望他能回心转意。”她顿了顿,声音里带着无尽的疲惫,像耗尽了油的灯盏,“只要他能保持中立,像棵橡树那样麻木即可,但他却非要踏入死地,背叛别人为他的付出和信任!”
鸿敦?瓦莱深呼口气,仿佛感同身受般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阴影,那些山脊轮廓在朦胧中微微弓起,好似苍老驮兽那即将被压垮的脊梁,“您背负的太多,很多人被猪油蒙了心,不明白您的良苦用心,以至于步入迷途,最终摔得粉身碎骨!”他的话语刚落,一阵风吹过花海,卷起无数花瓣。
“您是我的长辈!”袒露心扉的列拉?瓦莱如释重负般催马前行,马蹄踏过路边丛生的野菊,金色花瓣簌簌粘在雕花马靴上,留下细碎的芬芳。她语气恢复如常,鬓边的珍珠坠子随着马匹颠簸轻轻晃动,折射出细碎的日光:“您也是我的知己,我珍视您如同曾经珍视西阿翁。这样的付出是对美好的向往,虽然会付出代价”春风掀起她的面纱一角,露出嘴角释然的弧度,像冰雪初融的湖面漾开涟漪。
并马而行的鸿敦?瓦莱也长舒口气,腰间的和田玉佩碰撞出“叮咚”脆响,肥硕的身躯在马背上微微晃动,压得马鞍出轻微的呻吟:“每个人最难的就是要面对自己愚蠢的那一面,都需要珍视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,而不是带着毁灭结局的妄念!”他抬手抹去额头的汗珠,阳光透过指缝在他花白的胡须上投下细碎的光斑,与甲胄上的铜钉交相辉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