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叶书库>宫女回忆录 > 番外 蒋姝卿番外(第4页)
番外 蒋姝卿番外(第4页)
阿舒死在了成婚两年後的某个午後,一个极平凡的春日。
昨日他还笑着许诺,要带我去逛一场盛大的庙会。
。
那段时日的事情,我如今已记不太清了。
真奇怪,明明那麽珍视同阿舒有关的一切,可他死去那麽痛的事,我却有些记不清了。
断断续续的一些片段,是我被关在了屋里,如同当年瘟疫那般与世隔绝。
身边到处都是血,却都不是我的。
我睡在血泊里,身下的血热了又凉,滑腻而粘稠,比眼泪的滋味好。
兵刃的触感也记得几分,我想,那时候我大约杀了人。
杀了谁,我却不记得了。
仆从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惊惧,有巫者莫名被请来为我驱邪。
他们说温婉明媚的沈夫人一夜之间疯了,拿着刀刃,见人就砍。
我突然变的力大无穷,难以控制,仆从砍伤了几个,但唯一杀死的,却只有一匹马。
我坐在破膛的马肚上,一刀一刀刺下,嘴里喊着褚辰的名字。
那匹马刚从遥远的诸城被送进府,我原本期盼了很久。
公婆无法,便只能找来巫者,用中邪的借口将此事遮掩过去。
这些我不记得的事由丫鬟复述时,我亦听的心惊,心中暗骂。
怎就没用成这样,去杀人却连府门都没能踏得出去。
。
阿舒的死去,成了沈舒两家衰败的楔子。
与西川的最後一战,褚辰大获全胜,凭着军功与为国雪耻的声望,携着新起的势力重新回归了大梁的权力中心。
封王之时,他的声势升至鼎沸,与太子分庭抗礼,二子夺嫡的局面已然明朗。
皇帝老了,他不再需要运用帝王术制衡皇子的争斗来维系皇权的平衡;苍老的帝王,需要的,是一场赤裸的权力厮杀,再等待胜利者继承他的帝位。
太子与褚辰你来我往,胜负难分,最焦灼时,年迈的皇帝突然倒在了早朝的御座上。
太子犹如天助,趁此得到了监国之权丶还直管了刑丶吏两部。
褚辰一时被逼入穷巷。
我们意识到,这是弄死他最好,也是最後的机会了。
阵营衆人骚动起来,几番筹谋後,决定从青夏入手。
从她入手,是我献计。
褚辰当年对我有过真心,也因如此,我对他的了解远胜旁人。
他对青夏,从不作侍候自己的宫女奴婢看待。
她是他的心,是他未曾发觉的半条命。
褚辰这样地狱都爬的上来的人,只有将心碾碎,才能彻底摧毁。
这是他暴露给我的软肋,没道理不好好利用。
再没有比青夏的背叛更致命的了。
只要抓来了青夏,哪怕她撑得过严刑拷打,可幻药丶蛊毒……我们有的是办法撬开她的嘴,把她锻造成砍向褚辰的最好一把刀。
于是,青夏成了那场“血亲冲煞”布局中,最为关键的一环。
可惜,我了解的只是十六岁的褚辰。
早已不知这些年的岁月,将他塑成了何种模样。
就如这场死局,明明已至绝境,可他竟也能凭着青夏,逆转了整个局面。
青夏用刑时流産,皇帝因“血亲冲煞”失败而吐血。时隔多年,太子同褚辰,再次大殿对峙。
相比多年前那个慌乱的雨夜,此时的褚辰,态度沉稳,胜券在握。
我们这些太子党,从布局人,转瞬之间变成了棋子。
直至太子被狠狠处罚,收回特权,才堪堪反应过来,或许自天子晕倒之初,我们就如蛛丝上的虫,被网罗进了圈套。
褚辰布了一场绝妙的局中局。
绝处逢生,化死作活,向来他最是擅长。
只是此局一环扣一环,太过天衣无缝的巧合,反倒有些显眼,并非不曾引起老皇帝的猜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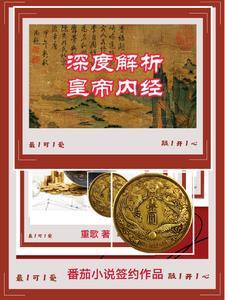
![[萌学园]飘啊飘的救援计划](/img/167432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