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叶书库>宫女回忆录 > 番外 蒋姝卿番外(第5页)
番外 蒋姝卿番外(第5页)
可他猜忌的是有人趁机利用“血亲冲煞”大作文章,却未曾怀疑过“血亲冲煞”这整个局的真假。
毕竟一开始,是太子占尽优势,几乎将褚辰逼入绝境。
可天子的猜忌很快就消散了。
因为,流産的是青夏。
但凡换任何一名女子,他都会怀疑褚辰随便找个女人,利用“血亲冲煞”来构陷太子。
可怀孕的人是青夏。
我尚且看得透褚辰同她的情谊,何况冷待他多年的君父,自然更了解,他在青夏这里寻得的一池暖意,有多重要。
她肚子里孕育的,一定是褚辰的骨肉,是天家的血脉。
果不其然,青夏流産当晚,陛下就吐了血,彻底打消了怀疑。
多年过去,对于她的流産破局,到底是褚辰有意为之,还是当真天命难违,都已无迹可寻。
那场风波中留下的确凿痕迹,只有青夏酷刑下的淋漓鲜血,以及皇後丶太子的一败涂地。
。
我从沉梦中醒来时,贴身丫鬟正靠在床边打瞌睡。
掌心的伤口已被妥善处理,仍隐隐泛着痛。
痛感让思绪渐渐清晰,恍然发现自己大梦了一场。
房门被猛然推开,惊醒了瞌睡的丫鬟,她匆忙起身,还未来顾我,便被大踏步走进来的父亲深沉的脸色惊呆在原地。
“你前日入宫,怎麽惹着了陛下?”
我撑力起身,摆手示意上前的侍女出去:“怎麽了?”
“你知不知道!陛下要将你指给李侍郎三公子作续弦!”
李侍郎家的三公子?那个傻子?
我倚在床头垂眸不语,这态度激得父亲情绪又高涨了几分,不顾体面地嘶吼:“你倒是说话!”
“父亲大人,您想让我说什麽呢?”我擡眸,朝他淡淡一笑,“父亲要女儿说什麽,或者做什麽,直说便是了,您知道,我最是听话。”
父亲一时哑住,怔怔看我,脸渐渐涨红,张了张嘴,最终只吐出几个语音不明的单字。
蒋氏当家人离开的背影仓皇又落魄。
曾经繁盛的家族已破败如斯,家主尚且成了掌中玩物,难道还指望,我在那人眼中,仍是个人麽?
擡手从发髻中抽出那支锋利的素钗,近年来它总沾染我的血,周身慢慢有了丝微淡的血腥气环绕。
我将它抵在颈间滑动,寻找能够一刺毙命的好位置。
冬之夜丶夏之日,百岁之後,归于其室。
阿舒,百年太久了,我熬不过那样多的夏日冬夜,提前去找你好不好?我们同衾同穴,同泥土一起腐烂。
下辈子,你就作一棵挺秀的树,我呢,就作攀缘的蔹蔓,交错缠绕,咱们永远不分离。
。
平静地等待了几日,却并没有等到指婚的旨意。
这事便被当成了无稽的流言,飞扬了几天,也就渐渐散了。
可姨母自宫中递出的消息却说,那日李顺已侯在门外,只等褚辰下旨。
最终,旨意没下,是因为青夏为我求了情。
青夏。
时隔多年後,竟然再次听到了这个名字。
只要是参与过当年二子夺嫡的旧党,再次听到这个名字,内心都不会毫无波澜。
世人以为,如今的惠妃便是自清澜殿起就相伴在帝王身边的宫女青夏。
天子感念她的付出与陪伴,封她为妃,直至今日,仍是後宫里唯一的妃位。
天下人都称赞年轻的君主,善待旧人,重情重义。
唯有我们这些曾同他搏杀过的太子旧党,知道那端坐後宫里的女子,根本不是青夏。
真正的青夏,三年前就消失在了褚辰登基的雪日。
意料之中。
她陪他一路走来,早晚会引人注意,连我这样的後宅女子,都能轻易想到用她作刺向他的利刃。
青夏已经不适合再活着了。
解决掉她,再找个完美替身,既全了不忘旧人的恩义名声,又肃清了身後不谐的丝丝暗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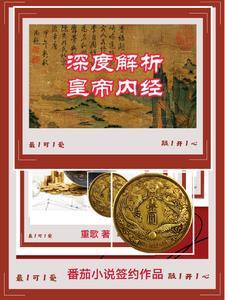
![[萌学园]飘啊飘的救援计划](/img/167432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