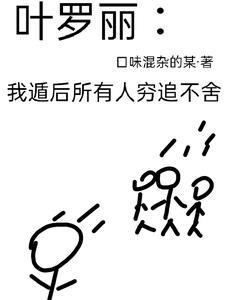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陛下难哄,那不哄了 > 4050(第27页)
4050(第27页)
陈怀衡看着她的掌心看得眼皮直跳,哪里又还有什么心情吃得下饭。
妙珠掀起眼皮看向陈怀衡,竟出奇平淡,她淡声问他道:“你满意了吗?”
她这样不也全然拜他所赐吗?
难道还不能满意吗。
陈怀衡抓着她手腕的手用力了几分,他反问道:“你自己不听话,要怪我头上?你总嫌我不拿你当人看待,现在我让人教你什么叫廉耻,教你读书,便又不肯听。”
妙珠听到陈怀衡的话,竟惊讶反问:“原来你是将我看做人了?”
哦,所以让嬷嬷来打她手板,不是想让她臣服于他,是想让她立身做人了啊?
他怎么说起谎话来,连脸都不要了呢。
陈怀衡听出她话中的讥讽之意,他捏着妙珠的脸问:“我不把你当做人,每日我又是和谁在床上交。欢?狗啊?”
陈怀衡看着妙珠那红掌心,那些干涸的血就像是一根根针,刺得陈怀衡眼睛都疼得厉害。
他语气不善,道:“总提从前的事做什么,都同你说过去了。不是读过论语吗,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知道?还总提什么。”
从前的那些事她怎就能记得这样清楚。
过去了不行吗,就因那三十板子,弄成这幅样子。
陈怀衡不是个会追忆后悔的性子,就像他口中所说那样,过去就过去,有什么好想,着眼当下不知道啊?非提那些糟心事来噎他。他现在待她不好吗?除了她惹他生气的时候,他还在什么时候欺负过她了?可是妙珠犟得可怕,竟让陈怀衡也生出一种极微的悔意,如果再回过头去,如果能再有一次机会
就在这样想着之时,妙珠却忽然看着他问:“你错了没,那你错了没有?”
妙珠仰着板子看他,她个头不高,大多时候总要仰视于他,从前看着陈怀衡的时候,眼中总是怯怯的,可是今日,她问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,眸光平淡,竟没有一丝惶惑不安。
陈怀衡听到她那话先是愣了愣,眼中都有些不可置信,她竟问他错了没?他错什么?妙珠脾气大便算了,现下竟还要叫他来认错,真叫她以为自己脾气好起来了?
陈怀衡下意识就想要开口讥她不知道天高地厚,然而那讥讽的话在触及她的眼睛之时,却又卡在了喉咙了里头。
他若是讥她,她又不知得一个人窝着气到什么时候去,一犯轴,就给他寻不痛快。
啊好,错了错了行了吧。
气什么呢。
怎么就气成这幅样子。
她给他低了那么多回头,他认一次得了呗,叫她心理平衡平衡,往后也不再瞎闹腾了,还给他戴一顶帽子出来,真给她能的。
陈怀衡说。
“错了。”
“我错了行吗。”
妙珠倒也没想到他竟真就这样痛快认下,她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?
她不敢置信地又问了一次:“你再说一遍?”
啧。
还得寸进尺上了呢。
陈怀衡瞥她,想把她抓过来啃一口,惩罚惩罚她这得寸进尺的小人样。
这股冲动压不住,他也确实这样做了。
他一言不合就捧着妙珠的脸去啃,嘴巴眼睛哪哪都不放过,一边亲一边又含含糊糊道:“我错了,错了,错了,行了没?舒服了没?得意了没?”
能不能不怄气了啊。
妙珠被他糊了一脸的口水,恶心地推他的脸,她道:“你认错就认错,动嘴做些什么。”
从前他总是逼着她认错,现在她总也从他口中听到“错了”两个字,即便不可置信,可待反应过来后心中也仍旧没有多高兴。
陈怀衡他又不是真心实意知错,她又能有什么好高兴。
他说错了,也无非是叫她再没借口去发脾气好了。
这样想来,妙珠才反应过来,自己给自己架上了。
可她问之前只是哽着一口恶气想和他作对,谅他不会应,谁晓得竟应得这般轻快。
妙珠想问他,你知道什么错了?让我们掰着指头好好算一算来你做的那些坏事。
你总喜欢在床上欺负我,错没错?你总喜欢贬低我,说什么礼义廉耻很多人都维持不起,错没错?你还总喜欢骂我小蠢货,错没错?还有三十板子,想起来就叫人生气,连个真相都不肯给我,错没错?你还不想叫我出宫,你凭什么,我到了年纪就是可以出去,错没错?还拿剑指我想要砍我,错没错?你错没错?你的错说起来扯都扯不完。
现在一个劲地说错了,他到底是知道哪门子错?
妙珠晓得,他只是想要稀里糊涂把这件事揭过去而已。
可那些以往发生的事妙珠再提他也不会认了,他一定会说,那都是过去发生的事了,逝者如斯夫呀,不舍昼夜呀,都不作数了好笑得很,叫她戳他一刀看他还作不作数。
他总说什么不作数,可又喜欢扯着她和陈怀霖的事情翻来覆去地说。
嚯,这样想起,更不要脸。
不过妙珠也不想同他计较,一会将他说得恼羞成怒了,最后又得叫自己吃苦。
听他认错,可她还是选择摘了眼前的事来发难。
她把那肿得老高的手伸到了陈怀衡的面前,“你还叫人打我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