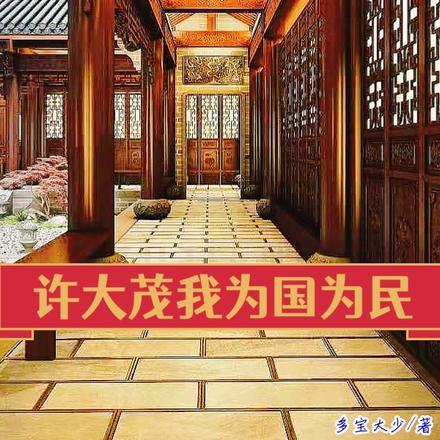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虐文女主,但痛觉转移 > 5060(第5页)
5060(第5页)
直到此刻方知,那被后世传颂的冠宠后宫,夫妻恩爱背后竟是藏满了龃龉与肮脏。
彼时尚且年幼的赵瞿,亲眼见证过父母琴瑟和鸣的感情,在撞破父母之间的龌龊后,该是怎样独自熬过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?
谢昭昭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赵瞿,毕竟今时不同往日,如今的赵瞿已是稳坐高位的越国天子,他不需要被怜悯,更不需要被同情。
他只是陷入了短暂的迷茫,急需要有人能伸以援手,将他从父母那段扭曲畸形的感情沼泽中拉扯出来。
于是谢昭昭这个毫无感情经历的爱情小白,便只能硬着头皮讲起了大道理:“这不叫爱,爱应该是希望对方好,不论何时都信任对方,不会背叛对方,不会伤害对方,只一心一意盼着对方过得好。”
赵瞿闻言垂下眸,似有所思道:“那朕不爱你。”
他并不完全信任谢昭昭,更谈不上什么背叛不背叛了,至于不会伤害对方这一点——从发现触碰谢昭昭可以缓解怪疾之后的每一日,平均每半个时辰他就会生出一次想要杀了谢昭昭的想法。
赵瞿又发出疑问:“那喜欢呢,喜欢又是什么?”
既然他不爱谢昭昭,那他为何会因她而茶饭不思,辗转难寐?
总要有一个合规合理的说辞。
赵瞿方才说话的嗓声不算小,谢昭昭自然听清了那句“那朕不爱你”,她嘴角轻抽了两下:“喜欢就是有好感。”
或许是怕赵瞿再追问什么叫有好感,她一步到位堵住了他的嘴:“有好感就是会忍不住去关注一个人,牵挂他,想念他,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追随他的身影,不管他做什么都会下意识偏袒他。”
话音未落,赵瞿便抬起眸:“那朕喜欢你。”
谢昭昭:“……”
赵瞿的告白来得猝不及防,明明是极有分量的话,便如此轻飘飘说出了口,却让人察觉不到一丝敷衍。
至少这一次,比起上次她生辰回家路上询问他“那陛下喜欢我吗?”,他想也不想便回答“喜欢”时显得真诚了许多。
或许是赵瞿盯着她看的眼神太认真,她心跳不合时宜地漏跳了一拍,下意识别开头抿紧了唇。
赵瞿却不让她逃避,修长清癯的手掌叩在了她的下颌上,硬是将她转回去的脑袋扳了回来:“谢昭昭,那你呢?你爱朕吗?”
谢昭昭被迫对视上了他的黑瞳。
这次他的眼睛不再像是初见那般黑洞般深不见底,她的眉目,她的唇畔,她睫羽垂下的弧度,每一处轮廓都清晰地倒映其中,仿佛世间万物都已散尽,唯有她是这方天地间唯一的真实。
谢昭昭当然可以做到面不改色的撒谎,但她却清楚谎言出口的瞬间,便会被那双眼睛洞察识破。
既然如此,又何必兜兜转转地白费口舌?
她张了张口:“不爱。”
赵瞿似乎并不意外,只自顾自接着追问:“你喜欢朕吗?”
这次他语气微颤,像是有些紧张。
谢昭昭默了默。
她其实从未认真思考过他们之间的关系,于她而言,赵瞿和赵晛没什么区别,不过都是她增长好感度,获得线索的工具人。
但仔细想想,赵瞿和赵晛之间还是有些细微的差距。
譬如此时此刻,若她对面的人是赵晛,她便绝无可能耐着性子与他回答这些幼稚无聊的问题。
什么喜欢不喜欢,这很重要吗?
谢昭昭盯着赵瞿看了一会,点了点头:“嗯。”
她不欲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,作答之后便立即将话题引回正轨:“陛下,我前两日做了场噩梦,梦见你在冬狩时遭人暗算,出了意外,身受重伤险些丧命。”
赵瞿松开了桎梏她的手,垂着头将兰草别在了腰间,语气略显漫不经心:“你在担心朕?”
赵瞿自然听出这场噩梦不过是个说辞,谢昭昭是担心他上次在赵引璋生辰宴上羞辱了橙家,橙家会因此生出异心,借此机会筹谋报复他。
她却不知,赵瞿便是在等着橙家报复他。
橙家是先皇一手扶持上来的土人首领,本是用来制衡北人的棋子,往日先皇在世时,橙家清楚自身权势源于皇恩,行事尚算谨慎。
但自从先皇驾崩后,那橙家便野心渐露,由太后把持着朝政近十载,为橙家谋取了数不清的油水与特权。
赵瞿走到今日,仍无法彻底扳倒早已在越国朝堂根深蒂固的橙家。
橙右相一贯是个小心谨慎的性子,明明暗藏祸心,却言辞恭谨,几乎让人寻不出一丝错处,这么多年在太后的助力下,于土人与北人复杂的局势中游刃有余。
要想让橙家犯错,必然要先给他们一个犯错的理由。
譬如上一次在赵引璋生辰宴为谢昭昭撑腰,这便是个很好的机会。
只是赵瞿没想到,谢昭昭竟是能自己猜想到这一层。
许是他的语气太敷衍随意,谢昭昭怕他不将自己的话放在心上,便也壮着胆子,学着赵瞿方才扳她脑袋的模样,伸手梏住了他的下颌:“陛下,我很担心你!我梦见你坠马,那匹马似是发了癫,朝着悬崖的方向横冲直撞而去……”
大抵是出了汗,她的手有些凉,但指尖压在他冰冷的皮肤上仍可以显出几分温热。
赵瞿被她僭越的动作搞得身形微微僵硬。
他还不太习惯她的主动,却并不觉得抵触。
谢昭昭认真地看着他,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:“陛下,你答应我,这几日狩猎不要骑马好不好?”
赵瞿:“……”
她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?狩猎不叫他骑马,那他应该骑什么出行?
他不语,便对视着她的眼睛,似是在等待她意识到自己言行举止上的冒犯和无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