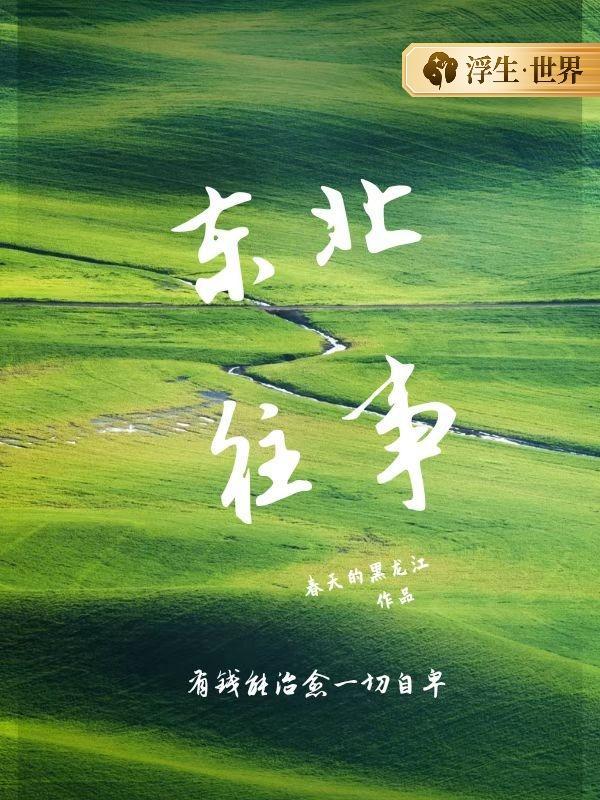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他人真好 > 第44章 异常(第3页)
第44章 异常(第3页)
卧室乱得像鸡窝,左一件上衣右一条裤子,杂乱堆沓,窗户紧闭,年轻男生的汗味在狭窄的空间里充盈、发酵,那种气味直逼胸腔口腔鼻腔上颚,天灵盖都蠢蠢欲动。
盛遇站在门口,微醺了两秒,扭头就走,“打扰了。”
卧室的门又关上,路屿舟逼着夏扬一起清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。
盛遇坐得无聊,又实在不想闻那股味,索性搬了把小椅子,进厨房坐着。
姨妈发现了他的存在,一边煎排骨,偶尔会朝他的方向看一眼。
锅铲刺耳的划拉声慢慢停歇,排骨炒熟了,姨妈往里倒了一碗话梅水,扣上锅盖,转小火慢炖。
盛遇跟同学开了一局斗地主,专注地算豆子。
周遭安静下来,雪白雾气升腾,他突然听到一句闲聊似的对话:“盛家对你咋样?”
“……”
盛遇茫然地抬头,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,冲蹲在垃圾桶边剥蒜的姨妈笑了一下,说:“很好啊,叔伯们都很疼我,您怎么突然问这个?”
姨妈背朝着他,坐在小板凳上剥蒜,手上动作一直没停,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,“我找人打听了,盛世集团很有钱……这种家庭,一般小孩都过得勾心斗角,提心吊胆的,兄弟间恨不得彼此去死,我看你的资料里没写这些,问问。”
市井小民对豪门的认知很匮乏,姨妈这段时日四处打听,加上一些自己脑补的艺术加工,盛遇在她眼里,已经是一个‘娘早死爹不疼,做小伏低,打小没有亲情,只有金钱’的可怜小孩。
盛家送来的资料很平和,不符合艺术加工,她半信不信,怀疑姓盛的做局骗她。
盛遇琢磨了下,顿时啼笑皆非,“您打哪儿听来的?您说的这些……也有,但这种情况我也只是听说,没亲见过。更何况盛家人少,斗来斗去早绝后了。”
他亲口说的,姨妈还是信了三分,紧拧的眉头微松,说道:“没有就好……我这两天老梦到你妈,她就留下你这么一个孩子,丢了十七年,我竟然一点都没发现,还得人家主动来通知我,她在梦里一直哭,说我这个当姐姐的不靠谱……”
盛遇一听,气氛不对,连忙把手机收了,拖着小板凳坐到姨妈旁边,歪着头一觑,姨妈果然眼睛红了。
他眨巴两下眼睛,笑起来,说:“那您跟她说呀,就说,孩子虽然丢了,但在外浪了十七年,又自己长腿跑回来了,他可聪明了。”
姨妈一听这话就没绷住,转过去拭了一下眼尾的湿润,哭笑不得道:“油嘴滑舌,你跟谁学的……”
生命中很多大事,不只有一瞬间的冲击,还有漫长的余震。
盛家找上门来那天,文秀感受不深,只觉得多了一个孩子,挺乖的,挺好。
后来她在街上看到一双球鞋,白色的,好看,适合盛遇。
付钱的时候,老板问要多大的鞋码,她愣住了,不知道。
那时文秀才意识到,这个本来应该在她身边长大的孩子,真的丢了十七年。
他的前十七年是一个可怕的空白。
当天晚上,她就开始翻盛家送来的文件……那群挨千刀的有钱人,不说人话,老用一些奇怪词汇,她只得一个个上网查,看了半个月还没看完!天杀的!
“不对。”一想到盛家人,姨妈又皱起了眉,把手里的蒜一放,拍拍手指间的碎屑,“现在没有,不代表以后没有,豪门大宅,肯定争家产,你以后要小心点,虽然你已经不算盛家人,但指不定谁暗中给你使绊子。”
盛遇没话好讲,笑道:“行,有人害我,我就赶紧跑。”
姨妈在围裙上擦了手,在口袋里摸索,掏半天,掏出一张银行卡。
“我跟那个姓盛的通过电话,姓盛的说,你和屿舟的花销都由他负责,但我觉得吧,人还是得自己有钱,才有底气。我给你和屿舟都备了一张卡,就当是你们的零用钱,哪天你要是跟盛家人吵架,别怕,腰杆挺直了,姨妈和棋牌馆就是你的退路。”
盛遇连忙推拒:“不用不用不用……盛家给的钱很多,够用,真的。”
姨妈瞪着他,一针见血地说:“你要是能安心花盛家的钱,你早前会搬来喜鹊巷吗?!”
“……”
盛遇舔着唇,有些心虚。
姨妈把卡塞他怀里,训斥道:“小孩子花大人钱咋啦!别的不说,你给姓盛的当了十七年儿子,收点精神损失费不过分吧!我一看他那个面相,子孙缘薄,捡着你算他撞大运啦!”
盛遇竟然有点被说服了。
别的不说,盛开济真是挺难相处的。
他揣着银行卡,摩挲着凸起的纹路,好半晌才轻笑道:“对,捡着我,算他撞大运。”
盛遇一直觉得,这桩身世是老天爷看他日子过得太舒服,凭空降的一道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