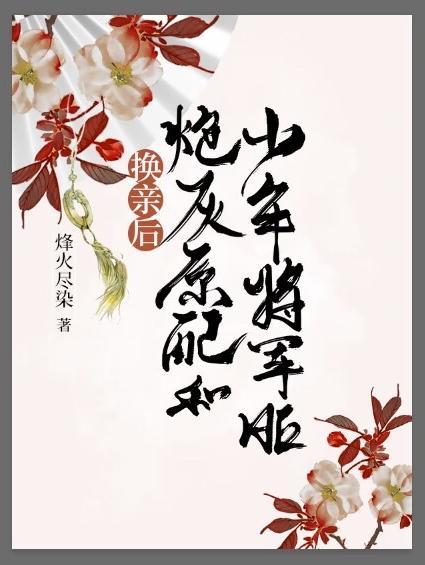一叶书库>快穿之带着直播间去古代 > 第286章 困惑与不解(第1页)
第286章 困惑与不解(第1页)
翌日清晨,天光未澈,裴府内院却已灯火通明。
两位小主子被精心梳妆。
裴谦身着浅青色圆领襕袍,袍料正是那价值千金的越州缭绫,在灯烛下流转着水波般的莹润光泽,纹样是符合他年幼身份的细巧缠枝暗纹,低调却不失雅致。
腰间系着五色丝线编织的宫绦,悬着一枚质地上乘、刻有瑞兽的白玉坠,寓意驱邪纳福。足蹬乌皮六合靴,纤尘不染。
裴婉的打扮更为精心。她身穿一件柔和的鹅黄缕金百蝶穿花襦裙,同样以缭绫为料,行动间如烟霞缭绕。裙摆层层叠叠,却丝毫不显臃肿,反显飘逸。
外罩一件绯色泥金绣缠枝牡丹的半臂,色泽鲜亮却不逾制,领口与袖缘以捻金线锁边,极尽工巧。
梳着双鬟髻,各簪一对小巧精致的珍珠梳,并几朵新鲜欲滴的时令宫花,颈项间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,项圈下悬着长命锁,锁上錾刻“福寿安康”字样。
腕上各戴一对雕花细腻的银镯,行走时清脆却不喧闹。
两个孩子被打扮得如同玉琢的人儿,周身却笼罩在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寂气氛中。
一切准备停当,府门悄然开启。
没有喧闹的送行队伍,一切都在一种刻意维持的、异样的平静中进行。
裴谦与裴婉由乳母及两位素有体面的老成仆妇引领,登上一辆青幄小车。
裴琰立于门内影壁前,并未送至府门外。他身姿挺拔如松,面色沉静如水,唯有紧抿的唇线和袖中微攥的拳头,透漏出一丝紧张。
马车缓缓驶离,车轮碾过青石板路,出单调的辘辘声,驶向那晨曦微光中巍峨矗立、象征着无上权力与命运的皇城。
青幄小车内部空间不小,陈设简洁却精致,铺着厚厚的软垫,以减轻路途的颠簸。
车辆微微摇晃,驶离了那令人窒息的府邸,车轮碾过石板路的“辘辘”声成了唯一持续的声响。
车内,年仅六岁的裴谦坐得笔直,小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。
他皱着小小的眉头,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
他偷偷瞄了一眼对面由乳母抱着的妹妹裴婉。她小小的身子几乎被包裹在华美的衣裙里,梳着精巧髻的小脑袋一点一点,似乎昨夜也没睡好,此刻被马车一晃,有些昏昏欲睡。
沉默持续了一会儿,裴谦终于忍不住,声音压得低低的,带着孩童特有的软糯,问向身边贴身照看他的老成仆妇:“阿嬷,我们这是要往大内去么?”他用了更符合当时宫城称谓的说法。
那仆妇身子下意识地坐得更直,声音压得极低,带着无比的敬畏回道:“小郎君明鉴。正是要入宫城朝谒。今日皇后殿下赐恩,于苑中召见宗室近支子弟。”
“小郎君与小娘子谨记礼数,垂恭听即可,小郎君与小娘子……或能得见昭阳公主殿下”
裴谦的小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昭阳公主……这个称呼他依稀听过,府中上下提及此人时总是气氛异样,下人们会立刻噤声,父亲的眼神则会变得复杂难辨。
他努力回想父亲今晨为他整理衣冠时,那低沉而郑重的叮嘱:“若见到昭阳公主殿下……需依礼恭敬,称她为‘母亲’。若她垂询家中事宜,你便禀奏:‘家中一切安好,唯……唯思念母亲。’”
可这又是为什么?他记忆中并没有这样一位“母亲”。他只有乳母和阿嬷。”
裴谦的小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他仰起头,眼中困惑更甚,声音里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:“为何独我与阿妹前往?阿耶……不一同觐见么?”
孩童的心思简单而直接,他将这几日府中异常压抑的气氛与自身联系了起来,心中不禁生出些许不安。
“可是因日前习《孝经》未熟,或言行有何差池,失了体面,此番入宫是去请训?”这个念头让他小小的脊背绷得更直了。